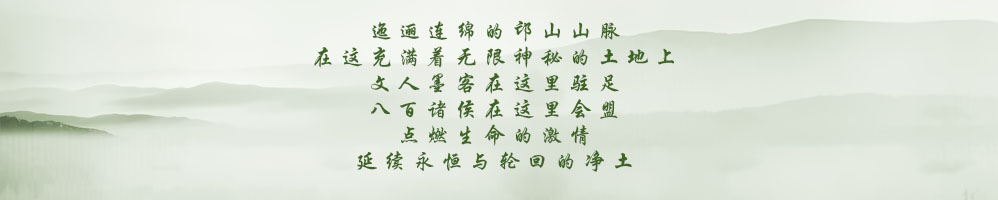殡葬礼仪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殡葬礼仪
丧礼--------吊唁
丧礼--------吊唁
---来自<朝阳陵园资料库>
吊丧一般从大殓之后开始,在这之前要把灵堂布置一番。灵前放一张桌子、悬挂白桌衣,桌上摆供品、香炉、蜡台和长明灯等。棺材下面放一只升,内装粮食,上插一杆秤,再放上一盏碗灯。旧时,人们对于尸体,灵柩,都忌讳停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据说,怕受所谓“日晶月华”,更怕冲犯上天过往的神灵,所以,停灵必须在屋内、棚内。总之,灵柩必须必须有庶盖。因此,在家停灵即便便是不预备酒席招待吊丧的亲友们,只要是举行个简单的祭奠仪式,就必须要搭棚。
当然,棚的大小及精美程度要视丧家的财力而定。灵棚是主棚。此外还须有许多用途不等,名目不同的棚,规模亦大小不一。由于治丧期问,吊唁的亲友多,而且时间较集中,祭奠时恐有发生拥挤的现象,甚至排不上号。所以在其他院落就要搭一座或数座祭棚,正面也要搭月台设位。凡属远亲、朋友来吊唁的,即被知宾引到这种棚里上祭。还有的棚是用来摆宫座。供来宾们休息、喝茶、用饭的。
一切准备就绪,就择吉“开吊”了。在吊丧过程中,死者守灵的家属对来吊丧的亲友,有一套繁琐的礼节。《仪礼·士丧礼》载:“君使人吊,彻帷。主人迎于寝门外,见宾,不哭;先入。门右北面。吊者入,升自西阶,东面。主人进中庭,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宾出,主人拜送于外门外。”
北京旧时的习尚,亲友至丧客吊唁,大门有门鼓,二门有梆、镇为之传报。窖至堋口,丧事人员便通知本家,喊道:“米客啦,本家陪灵您哪!”“某某老爷列!”或“泉某人太到!”来客不必投名片,士披上月臼,把铺在拜垫上的红毡子撩开。如果与奉家只足一般交情,与死者又是平辈,直接在红毡子上跪奠,本家也不会嗔怪。不过,恭敬一点的,还要撩肝红毡子,跪在白垫上;如是满人,即眭本宋仆役二人过来伺候奠酒,一人执壶,一人把盏,由把盏的将斟满酒的奠爵遵给来客,客人取手举过头顶之后,以左手端爵盘,右手执爵耳,洒入奠池里少许,递还执壶的仆役,随即叩首。如此三奠三叩。此时,官鼓大乐即以唢呐、海笛、堂鼓、九音锣为之吹奏,一奠一叩一棒大锣,极其庄重。如果是长辈祭奠晚辈,则采取站着奠酒的形式,谓之“立奠”。早时,女客都梳着大两把头,不便哈腰叩首,另有礼法。跪拜时,也不像男人把腰搬挺直,而是双腿一屈,坐在脚上,女仆伺候奠礼。行礼时,仅是头向右前方稍硝一倾,以石手指尖摩两把头衬的右翅,谓之“鞑儿头”,也叫“摸头礼”。清代,妇女叩奠都在灵后,本家女孝眷也跪在灵后右边陪礼。民国以后,男女姥都在灵前行礼。这样,本家男眷跪于灵左,女眷则跪于灵右。
浙江宁波一带的吊唁礼仪别具一格,其祭品也甚是风趣。灵前摆上由火腿制成的琵琶琴,用熟猪心作头,熟猪肺和猪肝作身,制成的姜太公,饰着彩带的白鲞,用熟猪肚制成白象,煮熟的鸡制作成的凤凰,悲悲切切的灵案上如一台小小的食品工艺博览,自是家眷对亡魂的一番心意和良好的祝愿。吊唁开始,爆仗齐鸣,礼仪程序颇有讲究,吊祭者均着素服,以亲疏尊卑为序,一家一堂,本家先祭,外客后祭,一律跪拜行礼,长者列前,晚辈于后,专设一赞礼生手持焚香一束,立于东首唱赞。另设一赞礼生于西首。东赞礼高唱:“一上香!”即递香给案前长者,由长者双手接香,高举额前,向灵位作揖后遂予西首赞礼生插于香炉。然后依次:“二上香!”团之上,拱手于额,随躬身之势双手下置左右,额角俯触蒲团。赞礼唱“伸!”拜者即起,垂手肃立。继之再复行再拜、再拜、三拜、三伸。礼毕,唱:“退!”祭拜者退两侧班再拜。在来宾礼祭时,孝子孝孙须匍匐案旁,磕头答礼。整个祭拜礼仪在爆竹声中结束。贵州贵阳一带的吊唁仪式限于三天内完成。第一天是“家祭”,第二天是“点主”,第三天是“客祭”。家祭时,亲戚们都要来到。门口请来的吹鼓手,客一进门时,他们就吹打一番。客人进来,先在灵前叩头,孝子(或晚辈)在灵后跪答。此后便是坐在客厅里,等着吃度。开席以前,“家祭”开始了:男男女女,分长幼跪成几排,道士叫着“献乐,叩首,献乐,叩首,献乐,叩首……三献乐,叩首。起……跪……”,大概总要半点钟,才开席。“点主”,并非平常人都能做,因为“点主”的人非名流或大官不可。所谓“点主”,就是请人在灵牌上的“王”字上加一点。“点主”时,在院子里置一方桌,上面铺红毯,置笔架笔筒朱碟等文具,椅子是太师椅。点主者坐着去接他的“八轿”--即八人抬来时,吹鼓手便先致欢迎曲,然后由孝子出跪在门口,将他请入,他走一步,孝子就得跪行一步,直至他走入大客厅为止。用茶毕,良辰到了,于是又由孝子去跪接他出来,即使没有太阳,他的头上也得罩上一把大红伞。他穿着大礼服--大袍、马褂,有的还带“顶子”,等叫礼者已叫毕,才坐在太师椅上。这时孝子便进去将灵牌跪行捧出来,在方桌前跪下。大概要奏乐数次,叩首若干次,这才将灵牌呈上大桌。在又叫又奏之后,点主者乃将新笔拿起来,此时便有人将孝子的中手指用针刺一下,叫礼者叫“取血”,点主者就用新笔去弄点血,叫礼者叫“点”,点主者就在“王”字上加一点。点完,就将笔向座后一抛。于是便有若干小孩来抢这支笔。据说这笔是非常吉利的,抢得以后,将来自有大吉利,因此,小孩们有时抢打得哭起来。随后点主者走了,走时也由孝子跪送。对点主者的报酬,通常是送一桌丰厚的酒席。客祭是比较随便了,总不外“叩首”之后吃席。
亲友来吊唁,大多要携带礼品或礼金的。礼金用黄色、蓝签的封套装好。正中蓝签上写“折祭×元”、“奠敬X元”。礼品有匾额、挽联、挽幛、香烛、纸钱、冥器等。挽幛无论质料如何,必须是蓝、灰、青、白等素色的,上边缀饰白纸幛光,写“英名千古”、“典型尚在”等。有的也送祭席,桌上压大幅的白色绸条,上书:“XX老大人(太夫人)尚飨”字样。秦晋北部及内蒙古西部吊丧携大馍馍(有的地方叫“点心”),至亲带整份儿,共12个,较疏远一些的则带半份。馍馍越大,表示其心越诚、其孝越甚。民间还有请僧人、道士做法事、行超度的习俗。
小敛、大敛、出葬离不开僧人做法事,即便是往后的头七、二七、三七……终七:百日、周年(小祥)、大祥,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反复不断地设立道场。
僧人设道场,道士们也可以设道场,为死人行超度。所谓超度,为道教施行的一种法事。通过此类法事,死者的魂灵就可以超越苦难,甚至飞升仙界,而不下地狱,也不受阴闻的任何磨难。在超度的诸多法事中,有两个项目值得提及。一是“炼度”。炼度要花数天时间。最初一天是“上表”:道士带领孝子,匐匐坛下,入定。“神灵’:接着携带着为死者赎罪的表文(表文由丧主背负着),“上天”面呈玉皇大帝。次日是“破地狱”。即仪式前用屋瓦将死者的灵牌覆盖着。法事开始,道士带领孝子设法将瓦打碎,从中取出灵牌。有些地方是事先用白纸制扎成一个四五尺见方的鬼城丰都的模型,并彩笔画出城门、城墙、宫殿的形状,置放在斋堂正中,道士诵经作法后,用力将手中的七星宝剑刺入城门,进而把整座丰都城戳得稀烂,砸得粉碎。在戳、砸之时,乔装成各种鬼魂的道士接连不断地往斋堂外逃窜。最后的一天是“炼幡”。它是炼度的核心内容和法事的高潮。其做法是先将书写着死者名姓的布幡折叠成一个小团,外边用耐火的盐卤布一层接一层地包裹,每包一层,便放置一种纸糊的物品,至少得包十层。包好的布团其外形好似莲蓬或者蜂巢。另外,还要包两个大小、形状完全与第一个相同的布团。这两个布团象征着金童玉女。布团包好后,在诵经声、音乐声中,将它们放进柴火中“烧炼”,不长时闯,抖掉最表面的包装,露出纸糊的物品,待此物品化为灰烬,再抖掉第二层包装,反复数次,直至写有死者名姓的主幡出现。这样,死者便在各种各样如火烧烤的灾难之中“超度”了出来。
二是“水火炼度”。行此法事时,道士在地上置水盆、火盆各一个,然后另一道士手举竹竿,竹竿上缠绕着无数丈长的纸幡,持竿道士手一抖,抖出几尺长的纸幡,随之放进火盆焚烧,再一抖,又抖出凡尺长的纸幡,再挑下来放进水盆中溶化掉,四五次后,手一抖,掉下一张几丈长的白纸条。白纸条既不置入火盆,也不放进水盆,而是被道士供养在案桌上,这就是所谓的“水火炼度”。经过“炼度”,死者就可以回转人世脱生了。
道士超度死者的时间由丧家决定,超度的时间可长可短,因此在剿义、葬礼、祭祀的各个节目中,都可以看到道士的身影。规模稍大一些的超度,丧家还要出资接戏班演戏。演戏的晚上还要燃放焰火。演戏、放焰火,表示超度的彻底成功,是一种庆贺的形式,因此丧事也随之演变成了“喜事”--白喜事。
事实上,丧事中的喜庆行为在我国广大汉族地区也大量存在,甚至沿习至今,愈演愈烈。汉族称丧事为“白喜事”。按理,“做七”期间,悲哀乃天经地义,可亲朋好友围坐餐桌前,大鱼大肉,吃得嘻嘻哈哈。喝僻酩酊大醉,仿佛不是在参加丧礼,倒更像是甩掉了一个大包袱。悲伤平?喜悦乎?在湖北清江中下游地区,出殡前一天的下午和傍晚,人们便开始向丧家所在的村镇集中。住在外村的亲戚一般包括死者出嫁在外的女儿及由婚姻关系带来的亲属,死者的堂、表亲戚和关系更远的亲戚;若死者为女性当然还有娘家的亲属。死者的女儿来参加丧礼,按常规要;譬一套“家业”(吹鼓手及吹打乐器),同时也带米夫家村落的一批亲戚、邻里。这些人或与比啬有姻亲关系,或与死者并不相识。但只要是去为丧家“跳丧”。人们也欣然前往。“跳丧”时,灵枢旁放置一面牛皮大鼓,一入坐在旁边击鼓并领唱,同时有两人或三人在灵前唱相并按蹦鼓点节奏跳动起来。跳丧者均为男性,除吒者直属外,来参加的人员都可以跳。舞者有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有中年人和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跳的人全身心地投入,不遗余力;围观者甚众,造成极其热烈的欢闹气氛。时常堂屋内跳不下,就到外面来跳。人们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围观者常跃跃欲试。将意犹未尽的舞蹈者挤出场外,取而代之。跳丧的同时,吹鼓手坐在灵堂外面亦不时吹奏一段。常常是一番丧鼓,一番吹奏,交替不已,直到天明。这种自演自观的歌舞形式造成极其喜庆的丧礼陋境,在办丧事时却长歌当哭,蹁跹起舞,甚至还要唱戏,其热闹的气氛与婚礼一般;有些地区吹鼓手在婚事和丧事中所奏的乐曲甚至也完全一样,故而林语堂先生在谈到中国的葬礼和婚礼时说:“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婿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找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
这些矛盾心理,折射出入们对死亡的某种相似的心理结构,这就是,人们对死者的眷念,实际是对生命的眷念;人们对死者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死亡的恐惧。如果说存在着敌意的话。人们的对死者的敌意,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敌意。人们的“喜”也不是对死背的“喜”,而是对自己未来的死亡示威:它既反映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又体现了人炎对这种恐惧的征服。一言以蔽之,人们在对死者的丧葬仪式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生死观,生之眷恋与死之恐惧,这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白喜事”之所以“悲喜交加”的真正根源。
还有,把丧礼办得热热闹闹的,也使人们变得乐意参加。人们前来参加丧礼,却如同来赴一次宴会。并且可以于此尽情地表黠心迹,宣泄情感,显示技能,这使丧礼实际上成为人们聚合、联系、交流和娱乐的一次机会。而丧葬礼中的宴席,更加体现了和乐融融的氛围。丧家要无所遗漏地请到邻里乡亲,奉酒饭以表示对众人前来吊唁和帮忙的报答酬答。到丧家坐席吃饭,是给面子的事,作为乡亲通常也不能拒绝。吃喝,从来是沟通某种关系或凋和某种关系的必要手段。在酒酣饭足之时,人们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而变得更加紧密。
- 上一篇:丧礼------守孝
- 下一篇:丧礼-----出殡